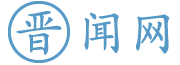| 本文涉及剧透,看片后阅读更佳哦!
我知道,很多人会在看完片后第一时间挑出一堆《寄生虫》的BUG。 
比如,社长一家(尤其是太太)为什么那么傻白甜那么好骗?为什么宋康昊一家每个人都有那么强悍的职业技能,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接手一个新工作后漂亮地做好自己的差事?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在地下室生活好几年毫不留下痕迹,不被发现?以及,为什么宋康昊最后要捅社长那一刀?
在纠结于这些剧情的不合常理之处前,必须先厘清的一点是,《寄生虫》并不是一部写实的现实主义电影。从一开始,奉俊昊就表明了是在构建一个精巧的寓言。

片中每一个看似出自生活的人物,其实都是一个象征,一种符号,一件功能明确的“道具”。 他们,以及片中最重要的两个场景——社长一家的豪华宅邸和宋康昊一家的半地下室,共同构成了这个寓言,让它变得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游戏。 分别代表了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的两家人,被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骗局给紧密联系在了一起。 
从基宇担任英语家庭教师开始,到基婷扮演美术老师,再到宋康昊顶替了尹司机,直至忠淑顶替了原本的管家。 最后,宋康昊一家四口,就这样“占领”了社长的家,那所充满了艺术和设计感的豪宅。 当这场精心设计的占领计划宣告完成之时,整部电影也就此被一分为二。从那个突然骤至的暴雨夜开始,事态开始逐渐失去控制,宋康昊一家的成果开始也开始一点点流失。 
雨夜在豪宅里的这场戏,也是全片最出色最巧妙的一场戏。
从宋康昊一家在客厅里胡吃海喝,到前管家突然到来把他们带入一个阴森恐怖的秘密地道,再到社长一家突然回家。事件经过了两度大幅反转,而最后的结果,是让茶几底下的宋康昊一家和沙发上的社长夫妇,第一次共处一室。 在如此近距离的对比当中,两个阶层的差异被赤裸裸地呈现了出来。底层的欲望如此真实和直接,而上层的欲望却不知包裹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伪装。 社长夫妇欲拒还迎的互摸,揭开了这层伪装的冰山一角。他们的欲望,需要更加下流的想象(那条廉价的内裤)和更加禁忌的行为(毒品)才能得到宣泄。 
在那个时刻,上层显得更加下流,而底层反倒显得有那么一点可爱。
这场戏的另一个妙笔是,当社长夫妇突然宣布回家时,宋康昊一家不得不立刻抱头鼠窜,想方设法躲藏起来。 他们在巨大的客厅四处逃窜,最后不得不全都挤缩在狭小的茶几下的样子,像极了蟑螂——或者也可以叫“寄生虫”。 在影片开始不久,他们在半地下室的家里坦然接受杀虫剂的洗礼时,他们作为“寄生虫”的命运其实一早已经注定。 作为他们的同类,那对躲藏在地下防空洞里的管家夫妇,则是一个更加荒诞、更加阴暗的“虫类”写照。他们除了生存,别无所求。

而反观社长一家代表的上层社会,他们衣食无忧,自然不必为生计发愁。他们不必与人争抢,而且还时常慷慨地给与。 他们关心的永远是子女的教育和成长,是公司的产品与收益,是光鲜的脸面和名号的虚荣。当他们兴高采烈地张罗儿子的生日派对时,他们显然不会注意到忠淑要一个人准备整桌宴席,宋康昊手里的购物篮早已不堪重负。 所以一个胡编的英文名和网上抄来的专业名词可以唬住他们,一张印刷精美的名片可以轻易欺骗他们,一条突兀出现的内裤可以神奇地策反他们。

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行为,其实背后统统有着属于那个阶层的心理色彩和动因。我们之所以看上去觉得虚假,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本身也与那个阶层隔着一段天然的距离。 奉俊昊把底层的贪婪与卑劣,描写得活灵活现。与此同时,不太容易被人注意到的是,他其实也把上层那种精致的虚伪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前者无耻,而后者傲慢。 还是在暴雨夜那场戏里,奉俊昊开始着意凸出社长的傲慢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宋康昊一家那种独特的气味,而且总是嫌弃地用手捂住自己的鼻子。 在最后高潮处的派对乱局中,这种傲慢还加上了几分冷血。社长在眼见有人流血受伤后依然自顾自地逃走,这个举动也成了压倒宋康昊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
归根到底,在社长的眼中,一切都是可以用钱购买的。豪宅可以,公司可以,佣人可以,司机可以,他们的尊严可以,甚至他们的性命也可以。 而让宋康昊从压抑到爆发的最关键因素,恰恰不是他本来最看重的钱,而是尊严的失去。是因为感觉到了社长那种骨子里对他的蔑视,让他捅出了那一刀。 
最终,影片前半段所有的精心设计,都被后半段种种的出乎意料给洗刷得一干二净。短暂地被联系在一起的两家人,还是回到了最初他们各自的样子。
社长一家在另一座豪宅里安然自得,而宋康昊一家还得回到自己的半地下室里。后者无疑更悲惨一点,基婷不幸丧命,宋康昊自己还被迫藏匿在了那个更加暗无天日的防空洞里,当一只看不见的“寄生虫”。 
他们此前所有逃离悲惨生活,向更上阶层迈进的努力,都以失败告终。而那个有朝一日买下那座豪宅的愿望,最终也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。如果说这场梦一度看上去将要实现,它也会被一场暴雨轻易打碎。 整部《寄生虫》也像是一场游戏一场梦,当梦醒之后游戏散场,上层与底层之间的断层,依然是无法跨越的鸿沟。 
奉俊昊并不试图支持哪一方或批判哪一方,他只是尽量生动地把双方描绘出来。如果说他有什么态度,那这种态度也是对双方的嘲讽。 他拍这部讽刺寓言的全部诉求,是用令人折服的技巧,完成一次无需深刻的讲述。 这是《寄生虫》作为一部类型片的使命,也是它作为一部类型片的至高成就。

陈熹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