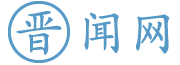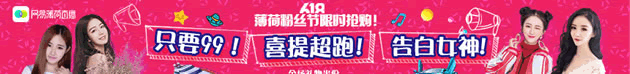过去的10年间,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前仆后继的出现了一批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,人口过千万的超大型城市。
整个东三省几乎是连片的人口流失,西北地区呈现出星星点点的斑驳,除此之外还有以湖北为代表的部分中部省会。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吴康副教授,采样了全国694个重点城市,做过一份关于人口流失的报告。在2007-2016这10年间,中国有84座城市都经历了连续3年或者3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减少。
伴随城市化的推进,中国的人口分布越来越呈现两极分化。趋利避害的人民用脚投票,快速并大规模的向东部、向城市群集中,催生了千万级的超级城市,也导致了地级城市、县级城市和乡镇的人口坍塌。
在城市化的轰隆声中,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资格成为北上广深杭、成渝、武汉、郑州……
即便中国1/5的城市已经发生了人口流失,但几乎所有的城市在编制城市规划时,仍然坚持预测人口会增长,城区要跟着扩张,新区还得建。
在84个人口流失城市的那张图中,吕梁横亘在中央,大而醒目,市区常住人口已经连续3年出现了流失。
但吕梁在2013年的规划中,仍然坚持按照“人口年增幅10%”的目标规划。
村镇上拉起了隔离墙,墙上挂满了宏伟蓝图,体育中心、写字楼、街区商业……一应俱全。
1年后,把吕梁新城作为1号工程的吕梁前市长丁雪峰被双规,吕梁新城戛然而止。
而吕梁新城原址上的大武镇已经有9成的建筑被拆迁,断墙残垣之上被蒙上厚重的灰尘,有人留在残存的街道上,有人搬回了吕梁山的窑洞里。
黑龙江的伊春,人口从上世纪80年代已经出现流失。但在2001年的总体规划中,仍然提出了“5年达到133万,10年突破140万”的目标。
新区建起来了,遗憾的是:直至2010年,伊春的人口也只有115万,时间已过5年,人口远未增长。
人口破千万的超级城市,每天都有相当基数的流动人口涌入,却在拼了命的控制用地红线,卡死用地指标,供需失衡的尴尬始终得不到最终的解决,甚至是暂时的缓解都做不到;
而诸多三四线城市,逐年都在确定的发生人口流失,却按照人口增长的假想目标,制定不切实际的规划,拼了命的扩大城市边界,建设新区。
解决的办法其实很简单:控制扩张欲望,按照人口流失的预期,把规划做小,把城市收缩。
你竟然不知道,财政转移支付、建设用地指标、基建投资、公共设施投资都是和人口挂钩的!
在当下的规划体系里,只有先预估人口增长,才能有城区面积的增加,才能获得财政支持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,才能有GDP的增长。
中国的大学里,关于城市规划的套路统统是,先预估人口增长,再匹配土地扩张,接着画路网、制定空间布局、配置不同功能、基础设施引入……
我们的城市化目标是如此的根深蒂固:只要有城市化,就必须要有增长,拒绝一个城市被打上人口流失、收缩的标签。
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开始的“抢人大战”,将会加剧这种极化,大者恒大、小着愈小。
也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必要按照超级城市的人口递增模板,做扩张的膨胀规划!
伊春和吕梁的案例告诉我们,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流失的,规划却是膨胀的,那么很可能导致一种结果就是:
伴随人口的流失,会出现房屋的空置,蔓延至建成区的连片空置;不切实际的扩张,不仅会加剧这种空置,还会引发公安交警、邮政快递、银行学校等公共服务的断层;最终,甚至会引起空间的破败、犯罪率的滋生……
在目前的国际上,“人口流失”和“城市收缩”已经不再是一个贬义词,而是描述状态的中性词。
在城市化的进程中,有人口增长,自然也可以有人口流失,有人口流失,自然也可以有城市收缩。
遭遇人口流失的其他城市,就开始严控扩张红线,中心城区之外的区域公共服务受限,引导人口回流至中心城区,同时在中心城区进行“城市更新”,保证留下来的人能享受到最好的公共服务,同时也节省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。
中国绝大三四线城市,真正需要的恰恰是中心城区的“城市更新”,而不是成为“新区狂魔”。
文章部分素材来源于清华大学龙瀛博士《收缩的城市》,感谢龙瀛博士及团队在中国城市规划研究中做出的贡献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