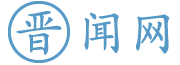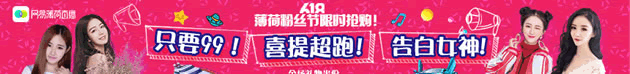总之,儒家“大同”社会理想不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乌托邦空想,而是一个可望可及的社会理想。“大同”并非完全的同一,而是有差异、有私产、和而不同的和谐和平社会。
《礼记礼运篇》首次提出了“大同”之说。记曰:昔者仲尼与于蜡宾。事毕,出游于观之上,喟然而叹。仲尼之叹,盖叹鲁也。言偃在侧曰:“君子何叹?”孔子曰:“大道之行也,与三代之英,丘未之逮也,而有志焉。”于是藉孔子言,描述了“大同”社会的情景:
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,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鳏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,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蔵于己;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,故外户而不闭。是谓大同。
这里需要分辨的是,《礼记礼运篇》所描述的“大同”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?是上下齐同、没有差异、大公无私的社会吗?过去有不少人是这样理解的,康有为就认为“大同”社会是一个无国家、无阶级、无刑罚、无私产甚至无家庭夫妇之分的乌托邦社会,其《大同书》写道:“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,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,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争、奸淫之防无爵位则无有恃威、估力无私产则无有田宅、工商、产业之讼。” |